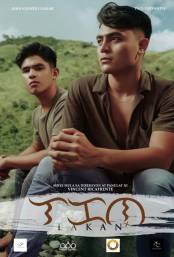【紙牌屋徵文-總統獎】從莎翁名劇 《馬克白》剖析《紙牌屋》
 2017-05-26
2017-05-26  2017-06-02 14:08
2017-06-02 14:08
◆本文為【美劇達人站出來!《紙.牌.屋》有獎徵文活動】獲選總統獎文章◆
「世界上有兩種痛苦,一種令你強壯,另一種毫無用處。那種無用的痛只有痛苦,我沒有耐心浪費時間在這種無用的事。」
“There are two kinds of pain. The sort of pain that makes you strong, or useless pain. The sort of pain that’s only suffering. I have no patience for useless things.”

《紙牌屋》(House of Cards)的主角Frank Underwood經常會以打破第四面的形式與觀眾對話,這類的影片拍攝手法以術語來說是:打破第四面牆,主角會對著鏡頭與觀眾的對話,這樣手法在影劇中多見,有些觀眾批評這樣的手法容易使觀眾出戲,但在本片中,Frank的對話卻帶給人一種恐懼感,與其說是單純交代細節或是人物心理,這些對白更像是畫龍點睛一般把人物形象在觀眾眼中做一個鋪陳。
但是,這對話卻產生了一種不同的感受,因為觀眾都相信跟主角本身是處在一個私密的對話空間,人在私密的對話空間中會顯現出:脆弱、虛弱的一面,但在本劇中恰恰相反,其所展現的是:暴力美學,一種安靜到空白;令人窒息的病態美學。
《紙牌屋》如同美國版的《馬克白》,其所製造出的不只是悲劇;也是種恐懼。

為何說是悲?因為在常人眼中看來,主角對於權力、名利的追逐、所捨棄的道德良知令人感到悲哀,這人,為此喪心病狂了!但又因為手法的殘暴,震撼了我們的道德良心,有操弄人的手段、預謀犯案、與對他人的漠視,與馬克白的不同的是,Frank並沒有因為動手殺了人而亂了手腳,卻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心。
有人曾說:馬克白是莎翁一齣到了現代還能夠被接受的戲劇,因為我們過了四百多年依舊是一群人「貪婪的人」,是的,我也是這麼認為。
在《紙牌屋》中,所有原本馬克白懦弱無能的特質都從《紙牌屋》中被去除了,而兩者之間還有很多共同點,無論是Frank或是馬克白,其懷有不可一世的自信、身邊都有一位能幹、想當上后的女人,中心耿耿的貼身侍衛,被看好、被預言、被背叛,最後當上王等等特質,是,在《紙牌屋》中,雖然手法冗長了一點,但Frank確實是刺下國王(總統)身上那一刀的人,就跟馬克白一樣。
但馬克白如果沒了夫人,就沒有馬克白了,如同馬克白夫人被譽為最難演出的角色,Claire的角色也是。
Claire扮演第一夫人的凶狠確實恰到好處,玩得起同樣陰險的心機遊戲,私底下道德良知與平凡生活的掙扎,跟馬克白夫人真是如出一轍,但殘暴殘忍之中,因其女性特質而又帶出的一些柔性、卻又讓人捉摸不定的心理特質,異端的冷靜,提供明智的言論,以及某些橋段表現出的痛苦與情緒折磨,成為了本部片的亮點。

以現代女性觀點來看,Claire並非單純的依附丈夫來獲得她的權力與社會地位,她自己也有一份工作,這女人有著縝密的心思、高雅的品味,以及宏觀的視野,也因此,她儼然就是Frank的最佳搭檔,與馬克白有些微不同的是,因為設定背景年代,那時候的女人需要依附丈夫來獲得名利,但馬克白夫人在危機處理上:如安撫馬克白、與馬克白商討計畫、看著發狂的丈夫、處理賓客等等,這些都能顯現出她是一位多堅毅而能幹的女子,也因此,她對權力的渴求是如此的昭然若見,是,這兩位都是渴望權力的女人。
但在追求了權力之後呢?或許最大的恐懼來自於並非來自對權力的渴望,而是對於權力受到威脅的恐懼,這種恐懼無法被澆熄,只能透過無限的謊話、殺戮、手段和循環來維持,一場爭權鬥利的背後,還有一場,那最後不論是馬克白、或是Frank到底追求的是甚麼呢?皇冠、名、利?我想都不是,令人所渴求的,或許只是心理上的快感罷了!
「熄滅吧,熄滅吧,瞬間的燈火,人生只不過是行走著的影子,
一個在舞台上高談闊論的可憐演員,無聲無息地悄然退下。
這只是一個傻子說的故事,說得慷慨激昂,卻毫無意義。」
-- 《馬克白》莎士比亞
(Out, out, brief candle! Life's but a walking shadow, a poor player
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
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. It is a tale
Told by an idot, full of sound and fury
Signifying nothing.)
-- 《Macbeth》Act 5, Scene 5, Lines 17-28
作者:藍獅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