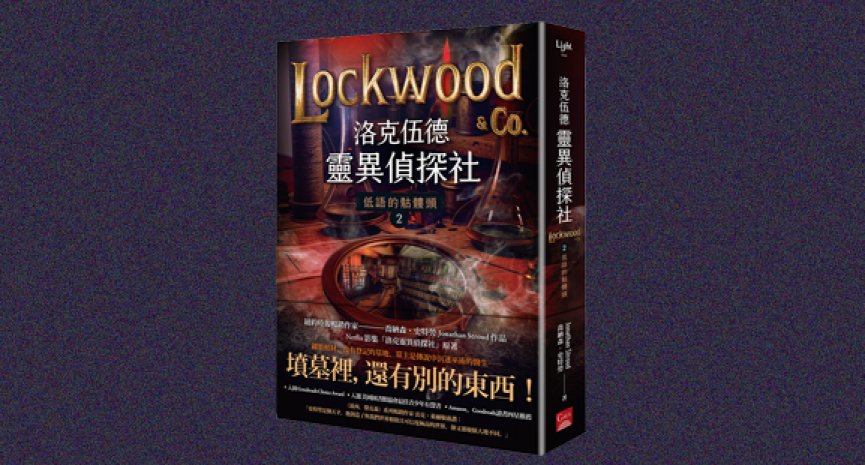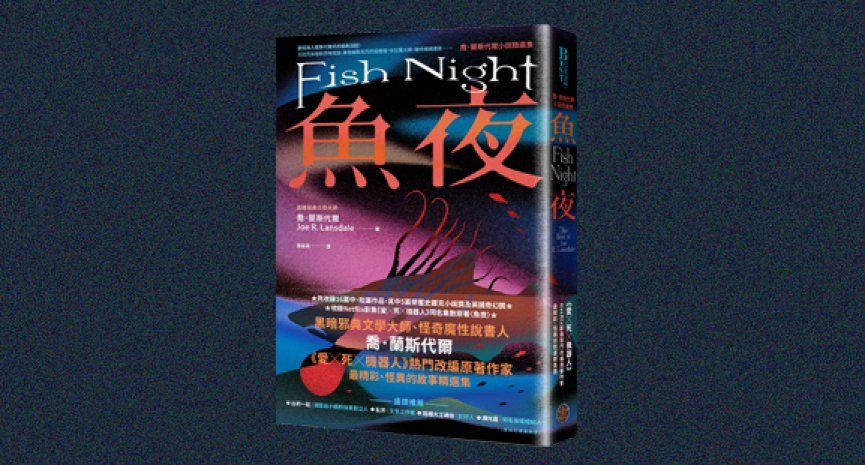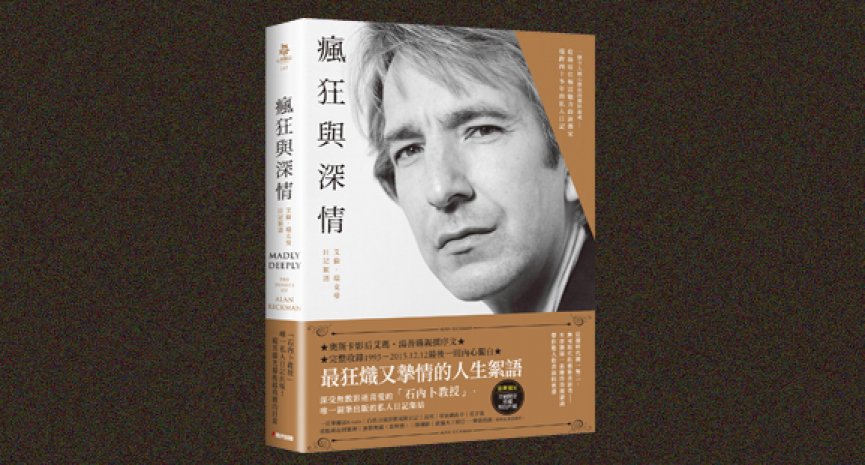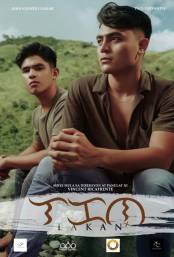《流沙刑》:直到法院判決有罪之前,任何人都是清白的
 2019-04-11
2019-04-11  2019-04-11 15:38
2019-04-11 15:38
文|莫琳派森吉莉特 (Malin Persson Giolito)
譯|郭騰堅
教 室
丹尼斯倒在左邊那排長凳上。一如往常,他穿著印有廣告的T恤,大賣場撿來的廉價牛仔褲,腳上的運動鞋鞋帶還是鬆脫的。丹尼斯是烏干達人。他號稱自己十七歲,看起來卻活像個已經二十五歲的肥男。他修讀汽修班課程,住在索倫蒂納1一座專收他這種「未成年」難民的寄養家庭中心。薩米爾就倒在他的旁邊。我和薩米爾同班;他通過了學校舉行的國際經濟與社會科學特殊課程檢定,我們才成為同學。
班導師克利斯特,就倒在講桌旁;他自命不凡,總想要「讓世界變得更好」。他的咖啡杯早已從桌上滑落,咖啡滴在他的褲管上。艾曼達就坐在不到兩公尺遠的窗戶下方,身體靠著暖氣架。幾分鐘前,她全身還是喀什米爾羊毛衣、白金鍊、涼鞋的打扮。她在我們接受堅信禮時收到的鑽石耳墜,仍然在初夏的陽光下閃閃發亮。但現在看到她,你可能會覺得她全身泥濘。我坐在教室正中央處的地板上。瑟巴斯欽,全瑞典頭號富豪克萊斯.法格曼的兒子,就倒在我膝前。
教室裡的這幾個人,很不協調。我們這些人通常不會一起混。或許會在計程車罷工時的捷運站月臺上,或是火車的餐廳車廂上遇到,但不會在教室裡。
一陣類似臭雞蛋的氣味飄過;灰濛濛的空氣裡,散發著濃濃的硝煙味。除了我以外,所有人都中彈了。我所受到的,不過就是一塊瘀傷。
案件代碼:B147 66審訊
地方檢察官 對瑪麗亞.諾貝里的起訴
開庭首週:星期一
1
第一次見到法院室內時,我覺得很失望。那次是我們班級旅行的訪程。我很清楚,瑞典法官不會是頭戴假鬈髮,身穿長袍的佝僂老頭;被告也不會是穿著橘色囚衣,嘴角噴著口沫,腳踝銬著腳鐐的瘋子。不過,我仍然很失望。那個地方,有點像社區醫院和會議中心的混合體。我們搭乘一輛散發出腳汗與泡泡糖味道的出租巴士,到達法院。被告滿頭都是頭皮屑,衣服皺巴巴,被指控逃漏稅。除了我們班(當然,還有克利斯特),旁聽席上只有其他四個人。但是那裡座位很少,克利斯特只能從外面的走廊多搬來一張椅子,才有位子坐。
今天,情況可不一樣了。我們身處瑞典最大的法庭。法官們坐在天鵝絨面高椅背的暗色桃花心木座椅上。正中央椅子的靠背比其他椅子的還要高。那是首席法官的座位,他被稱為「首席法官」。他前面的桌子上,擺著一把手柄包覆毛皮的大頭錘。每個座位前方都有細長的麥克風豎起。看似橡木製成的壁板,彷彿有數百年的古老歷史;這裡的「古老」,是正面的意涵。座位間的地板上鋪著暗紅色地毯。我從來就不想面對群眾;我從來不願加入聖露西慶典的唱詩班,或參加什麼才藝比賽。但現在,這裡面卻已座無虛席。而他們全都是為我而來;我就是焦點。
我身旁,坐著我那些個來自桑德暨賴斯達迪斯律師事務所的辯護律師。我知道,桑德暨賴斯達迪斯這名字聽來很像一家古書店,店裡還有兩個大汗淋漓、戴單片眼鏡、穿絲質大衣的男同志,手提煤油燈,步履蹣跚,拍掉發霉書籍與動物標本上的灰塵。不過,他們可是全瑞典最專精於刑案辯護的律師事務所。一般刑事犯都只有一名疲倦不堪的公派辯護人;而我的律師則帶上了一整票興奮的職員,還穿著模仿秀演員常穿的那種西裝。他們在斯德哥爾摩舊城區艦橋路上一間超炫的辦公室,工作到凌晨時分, 每個人都至少有兩支手機,除了桑德以外。他們活像以為自己在演美國電視劇,用一副「我好忙,我很重要」的表情,吃著外帶的中國菜餐盒。桑德暨賴斯達迪斯律師事務所的二十二名職員中,沒有人名叫賴斯達迪斯。叫這名字的人早就死了,想必是死於心臟病,死因想必也是「我好忙,我很重要」。
現在,我的三位律師都在這裡:名人彼得.桑德,以及他的兩位同事。當中最年輕的是個小妞,髮型凌亂,有穿鼻洞卻沒戴鼻環。也許桑德不准她戴(「馬上把這垃圾給我拿掉!」之類的)。我管她叫「菲迪南」。
菲迪南認為,自由主義就是一種髒話,比核能發電還要危險。她想證明自己的性別地位獲得提高,因此戴著惹人厭的眼鏡;她認為資本主義是我的錯,所以對我很厭惡。前幾次見面時,她把我當成機上一名瘋狂的時尚部落格作家,拿著一個保險已拉開的手榴彈。「好的——當然!」她說話時, 完全不敢看著我。「好,好——別擔心!我們會幫妳的!」感覺像是我在威脅:要是你們膽敢在我點的有機番茄汁裡加冰塊,我就把所有人都炸飛。
另一位助理律師是個有著啤酒肚的四十來歲男子,一張圓臉活像煎餅,臉上的微笑彷彿在說「錄影帶在我家裡,我可是照字母順序將它們排好,鎖在保險櫃裡的」。啤酒肚男子理著短短的小平頭;老爸總嘮叨著,說沒有髮型的人是信不過的。但是老爸這個說法,想必也是從電影上「剽竊」來的,而不是自己想到的。老爸好俏皮,好愛說笑。
我第一次見到啤酒肚圓臉男時,他的眼神定在我鎖骨正下方,強迫自己把厚重的舌頭縮回嘴裡,愉悅地嘶聲說:「小姑娘,這怎麼行呢?妳看起來比十七歲大得多了。」如果桑德當時不在場,他想必就要喘息,甚至流口水了。讓口水一路從嘴裡流下,滴到有夠緊的西裝背心上。我懶得告訴他:我成年了,滿十八歲了。現在,圓臉男坐在我左手邊。他還把公事包,以及裝滿紙張與卷宗夾的滾輪行李箱一起帶來了。已經清空行李箱,山一般的卷宗擺在他面前的桌上。他留在行李箱裡的,只有一本書(《一舉搞定—贏家的藝術》)和一把從小內袋突出來的牙刷。老爸和老媽坐在我後方第一排的旁聽席上。
那次考察不過是兩年前的事,卻已如永恆一樣久遠。我們班在出發前還先演練了一次,目的是要讓我們「了解場面的嚴肅」以及「能了解現場情況」。我很懷疑這樣做是否有效。不過我們從那兒離開時,克利斯特說我們「很守規矩」。他本來很擔心,以為我們會克制不住,開始咯咯傻笑、喧鬧、玩手機。他以為我們會像那些無聊至極的立法委員,準備呆坐在那邊玩手機遊戲、垂著頭呼呼大睡。
當克利斯特說明,法院審判不是兒戲,會嚴重影響人們的生命時,聲音可是肅穆極了(「各位,給我聽好!」)。我還記得他的聲音。直到法院宣告判決,任何人都是清白的。他一再重複。克利斯特說話時,薩米爾正襟危坐靠在椅背上,用一種所有老師都愛得不得了的方式猛點頭。他點頭的神態彷彿在說:「對,我都懂!你說的我全——都懂!你說得真對,真行,我沒有什麼要補充的。」
直到法院宣告判決,任何人都是清白的。這是什麼鬼話?從一開始,無罪的人就無罪,有罪的人不就已經犯罪了嘛。法院會弄清楚事情發生的經過,而不是判定什麼是真的,什麼又是假的吧?警察、檢察官、法官們事發時都不在場,不知道誰幹了什麼,可不代表法院事後就能自作主張。
我記得,我跟克利斯特這麼說過。法院一直都在犯錯,強姦犯老是被判無罪。即使妳被大半個難民收容所的人強姦了,兩腿間還被插了一整箱的空酒瓶,他們就是不相信女生的話。針對性侵向警方報案,簡直是餿主意。而這也不代表:什麼事都沒發生,強姦犯啥事都沒幹。
「事情沒那麼簡單。」克利斯特說。
老師的回答都是些陳腔濫調:「很好的問題……」「我有聽到你說的……」「這種事不是黑白分明的……」「事情沒那麼簡單……」這些全都指向一點:他們連自己在講什麼都不知道。
不過好吧,如果要知道真相、知道誰說謊這麼難,我們無法確定時該怎麼辦?
我曾在某個地方讀到:「我們所選擇相信的,就是真相。」這聽來真是更混亂了。好像某人就能決定真假了?難道事情的虛實真假,會因為你問的對象而有所不同?是的,只因為我們相信的某人說了些什麼,我們就可以決定:事情就是這樣,可以「選擇相信它是真的」。怎麼會有人想到這麼白痴的事? 如果有人告訴我,他「選擇相信我」,我馬上就知道,他其實非常確信我完全在說謊,只是假裝成相反面罷了。